「如果我沒有做殯葬業,我沒有看過那麼多死亡,我沒有辦法體會,我也不會懂道愛、道謝、道歉、道別是什麼。」
台北永康街的一間咖啡廳裡,木色牆上掛著電影《送行者:禮儀師的樂章》海報,走進門的瞬間許伊妃的眼神就落到了海報上,「你特地選的?」她微微一笑。
2009年,16歲的許伊妃在一場告别奠禮上初識葬儀內容的莊嚴溫柔,從此踏入與電影主角本木雅宏相同的行業──殯葬業;入職八年光陰、超過兩千個日夜站在死生交匯的渡口,年紀輕輕的許伊妃用最深沉的方式親歷了生命的重量。
2017年,許伊妃出版個人第一本著作《黑暗中,我們有幸與光同行》,20個尋常的職場故事,她用簡單的文字,娓娓道出生命的秘密。
遺體不可怕
「不要叫我禮儀師、送行者」、「不要用『正妹』報導我!」許伊妃這個人很直爽,她拒絕任何刻板標籤。臉書上,她大聲宣告自己就是個「俗ㄅㄧㄚˋ(閩南語:俗氣)的殯葬業者」。親手為亡者上妝、沐浴,陪伴生者摺蓮花、度過告別式,從業多年,跑在生命終點「前線」的許伊妃從不忌諱談論死亡,但提及自己的工作,她總避開最令人不捨與殘忍的離別故事:「我覺得選那種最慘的就會扭曲我想表達的東西;變成好像又強化死亡很可怕,然後大家都對死亡又是一種害怕,不敢去正視它。」
電影《送行者》裡,本木雅宏第一次接體時因為忍受不住屍體腐爛的氣味,當場吐了出來;數年前,許伊妃第一次打開屍袋也聞到了同樣腐敗的氣息,只是自始至終,她不曾注意那股味道究竟具體是「酸」、「臭」還是「什麼」。在許伊妃的殯葬世界,遺體濃烈滲人的形象被抹去,大眾對死亡很單一的認識也在無形中瓦解。工作需要時,她甚至會親手牽住遺體緊握的雙手,讓對方「軟化」鬆開。
「不要說什麼『溫暖祂們』,這太道德了。」許伊妃形容某次情形,因為時間緊湊遺體必須盡快「放手」才有辦法戴上手套清潔,用吹風機慢慢退冰行不通,她便自己雙手用力緊握遺體,心裡默默跟祂說話。「當祂手真的打開的時候,我覺得那個不會動的遺體給了我一個很實際、很實在的鼓勵跟動力。」即便心裡清楚是活人的體溫在發揮作用,這個瞬間,許伊妃清晰地感受到了自己存在在這個行業的價值,還有這個行業值得的東西。
這是別人遇不到的,語氣裡挾帶肯定。「旁人再怎麼相信那是科學或宗教、相信手握祂祂會軟化放鬆,他也沒有機會去證實這件事情。可是我有,我有的話我為什麼不去試試看?」如果當時遺體不放手,許伊妃就會說服自己換另一種有力的方式幫助祂,「可當祂手真放開的那一刻,不管是實質工作還是心靈層面的收穫……」何不試試呢?許伊妃說,一切都很簡單。
其實遺體不恐怖,大家怕的也不是遺體,是死亡,還有遺憾這件事情。是害怕看到遺體之後想到的所有事情。

勇敢道愛
2017年終大熱的韓國電影《與神同行》探討死後題材,許多人在電影院裡流淚不止。「《與神同行》跟我的書《與光同行》講的是一樣的事情,就是無憾和後悔。電影就是在演生前可能沒有說的話、沒有圓滿的事情…… 我以為我會哭,但可能對我來講,我覺得就是應該的。我沒有這種困擾。」許伊妃開玩笑的說,她幫這個電影下了一個影評:「那些會哭的人一定沒有好好陪家人」。
每天及時而勇敢的向家人道愛、道謝、道歉、道別,是許伊妃「陪家人」的方式。睡覺前,她會把所有家人想像明天會死,然後把想說的話在當天就告訴他們,「真的,不誇張!然後明天起來他們都還活著,我都覺得我每一天都賺到了。如果明天他走了,我也覺得其實我昨天就已經想到了,而且我也告訴他了我愛他。」在旁人眼中「看盡無常」的行業裡修煉多年,許伊妃心底清楚,如果沒有勇氣面對明天的變化,死亡極其任性。
「你最愛誰、最怕誰躺在那裡,就勇敢的去陪他,去做到哪天他就算躺在那裡了,你也不怕,你也沒有遺憾。」
「你什麼時候覺得自己活著?」她忽然這麼問,明快的語調吐出犀利的字句。有人從痛苦裡經驗人生,有人因喜悅生發存在的價值,但是對許伊妃來說,生命的悸動不假外物刺激,存在的意義也無須特定事件激發。她給出的答案極其平實:「我覺得可以好好的呼吸,腳踏實地的去做每一件事情,然後正視死亡,那時侯就是活著。沒有太多想法,就是很純粹的生活著。」因為對死亡做足了準備,平凡日子裡的每一次波動和起伏,都屬於生命最真實的體現。
「如果我沒有做殯葬業,我沒有看過那麼多死亡,我沒有辦法體會。我也不會懂道愛、道謝、道歉、道別是什麼,」許伊妃很幸運,深淵裡她看見了生命的幽光。「可是當我遇到的時候,我去試試看這個東西,發現很實用。」這也是她寫下《黑暗中,我們有幸與光同行》的初衷。故事主角願意無私、勇敢的用曾經的傷痛幫她傳達這些訊息,她也希望讀者看完之後,心裡能有一絲改變與收穫。

悲傷輔導
喪葬儀式不全為了服務亡者,更多的是要撫慰生者;而殯葬人員的必備技能之一,還包括評估生者的心理狀況。要周到、圓滿的安頓家屬的心靈,殯葬人員得從接體的第一刻起,就開始蒐集拼圖。
為了引導家屬將悲傷釋放、不再背負更多遺憾,許伊妃曾「違反」白髮人不送黑髮人的禮俗,帶著一位父親跟隨出殯隊伍最後一次目送往生的兒子離去。「我還有遇過那種因為害怕從頭到尾沒有去看過遺體的,」許伊妃說。「但這時禮儀師就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,你要評估這個媽媽看了這個小孩對她心裡有沒有幫助,」她描述種種情境:「如果今天你的判斷是這個小孩不去看他爸爸,他一輩子會有遺憾,你再怎麼樣用關心的、再怎麼樣輔導、用逼的也得牽著他去看他最後一面,只要遺體的狀況不是太糟,不會影響到他後續的生活。」
在長達兩至三周的過程中,許伊妃蒐集到的碎片能幫助她了解逝者的個性與喜好,這不僅有助於喪葬儀式的安排更為體貼溫暖,也讓許伊妃和家屬建立了連結。告別式結束後她會持續關心家屬,當有人主動聯繫她、找她聊天時,她也能適時的給予輔導與協助。「人的悲傷程度是複雜的,」許伊妃說,當殯葬人員遇上深陷悲慟怎麼都走不出來的家屬時,只能協助對方轉介、求助更專業的人。
不是所有殯葬業者都會這麼做,但許伊妃選擇多留神一點。「應該是說你的用心跟付出勝過那些冷冰冰的專業,」很現實,她坦然表示:「你只要努力、只要把重心放在家屬這邊,你就算什麼都不會,他也會相信。」其實許伊妃過去從未接受這方面的特殊訓練,為何要在已經十分壓抑的工作環境裡傾注、共享自己的私人感情?「你選擇一個角色你要扮演好,」許伊妃這麼回應:「任何事情都是這樣,要演就要演長期的。」她直爽的比喻:「就像柯文哲講的,作秀會啦,但可能其他人經不起那麼長期的作秀,我『作秀』做了八年了,我可以很敢講。」至於那些曾懷疑她的熱忱不會持續太久的前輩或同業,許伊妃笑笑回應:「不好意思,我『演』到現在還在『演』!」

說真話的勇氣
過去,因為對死亡的汙名,人們對殯葬業的認知停留在一種不光彩的行業、甚至是「賺死人錢」的印象,業者時而面臨部分家屬的不信任與行業歧視,鮮少將他們的職場甘苦談大方分享到網路上。「我一直在檢討我們這個行業為什麼曾經讓人家這麼的不尊重、為什麼現在大家都覺得很辛苦,」工作時間不固定、突發事件不可控,這些客觀因素可以通過人員調配來解決,許伊妃說辛苦的是「我們的職業被冠上了一個『道德』」。
餐館到點就打烊,商店沒貨就停售,其實殯葬業也一樣,「我們就是服務業,」許伊妃說,「你有需求、我們給你。」但弔詭的是,儘管殯葬業者因為大眾對死亡的禁忌而遊走社會黑色邊緣,卻又因處理死生祭儀大事而被賦予了神聖的「使命」;就像醫生或老師,他們有權利對客戶的要求說「不」嗎?
「其實是有的,」許伊妃果斷點出:「我覺得這才是讓殯葬受人尊重的一個很重要的環節──你要勇敢的認清自己只是服務業。」《送行者》裡,廣末涼子為了丈夫的職業和他分居;現實中,真正因為殯葬業而離婚、影響私人生活的情況更是時有所聞。「我們都在用自己以為的道德包裝自己。原因是為什麼?其實是因為經濟壓力。」赤裸裸的答案既直接又現實,但許伊妃認為,撇除掉經濟負擔,其實殯葬業者不需要委屈自己。「家屬也不行看不起我們、也應該尊重我們,因為我們都有選擇,我們可以說『我不要接』。」
「人都要訓練自己說真話,」指出行業禁忌不容易,但許伊妃還是要發聲。她認真的說:「我覺得殯葬業的同行們應該也要努力,別讓金錢帶給我們的身分這麼多歧視與卑微。」搶屍體賺死人錢、年薪百萬與黑道掛勾,這些刻板印象與迷思不代表整個殯葬生態。「很多事情其實是之一,不是唯一。以前的生態或許是非要賺你錢不可,」眼神堅定,許伊妃的聲音清亮:「但時代在變,我們新生代的努力,也讓文化慢慢不同了。」
「我相信我們年輕一輩能用專業和態度讓殯葬的時代反轉。」

殯葬業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工作。入職八年,許伊妃見過叼著菸、拿亡者壽衣開玩笑試穿的前輩同行,也遇過治喪期間對業者充滿歧視與無禮的家屬,「但八年前第一次入行的時候我就告訴自己,我不要妥協那些黑暗的工作觀,」許伊妃說,唯一能做的就是「堅持」。
「感謝生命出現祢/你們,」她常常寫道。因為殯葬業,許伊妃在告別的遺憾中發現了溫暖和圓滿的可能;離開原來的崗位後,她也持續體驗不同的人生,寫文章、在各地演講,將生死的秘密分享給所有需要的人,希望繼續用生命影響生命。
或許對許多殯葬業者來講,許伊妃所透露的只是最簡單不過的故事,但「我是殯葬業裡面的淺水魚,看到的都是珊瑚和清澈漂亮的海水,」許伊妃說,她不是不能掌握殯葬世界的現實與辛酸,但她選擇留下美好的部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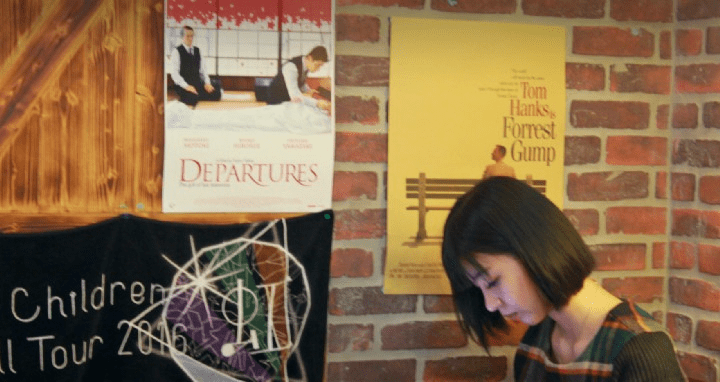
發表留言